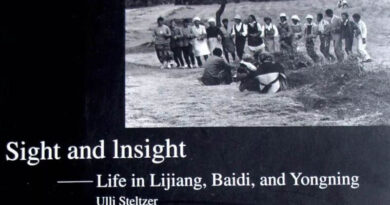昆明,京戏岁月
现今的戏曲,包括京剧在内,不是很景气,剧团似乎闲呆着,很少见他们的演出广告,海报就更别提了。记得以前,我说的以前是五十来年前,那情形可是大大的不同。印象最深的是关肃霜的海报,当时她和于素秋唱对台戏,盛况空前,五十多年后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早在关肃霜、于素秋她们来之前,京剧在昆明已相当盛行了。京剧的叫法文绉绉的,昆明人习惯上还是叫京戏。当时昆明专演京戏的剧场有三处,一处叫云南大戏院,在绥靖路(后改名长春路);一处叫西南大戏院,在东寺街;还有一处叫春明戏院,在民生街。那时年纪不大,看京戏就喜欢看武打戏。我家住在正义路文庙街口,离云南大戏院近,常去看有“活美猴王”之称的武生朱英麟的连台本戏《石猴出世》,对朱英麟佩服得很。加上杜老板杜文林妙趣横生的猪八戒,还有那海派的机关布景,太对一般市民和少年人的胃口了,一连接着演了好几个月。除孙猴子外,朱英麟的《铁公鸡》、《恶虎村》,短打功夫了得,很有看场。后来听说朱英麟是抗战初期从上海那边辗转来到昆明的。戏院的厕所在后台的东侧,观众去上厕所就能看见演员从后台口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虽然那片地方味道难闻,看演员的本相毕竟也是一道风景。我就想瞧瞧朱英麟,还真瞧见了好几回。
后来兴趣转移到春明大戏院的武生李毓麟、李幼麟了。我家也住福照街。福照街是老名字,后来改叫五一路。“春明”在民生街与福照街交会的丁字路口,离我家不超过两百米,看戏更方便。原先只喜欢朱英麟,对“春明”二李有些生,后来听说二李是两兄弟,或师兄弟,武打了得,便也去试看了一两回。一看还真不错,他们的《挑滑车》和《三岔口》确实出手不凡,《四杰村》和《金钱豹》也让人爱看。弟兄俩长靠、短打样样来得,尤其李毓麟,更让少年人迷醉。
二李属于剑佩平剧团,初到昆明驻祥云大戏院。平剧是三四十年代对京剧的叫法,当时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就跟着改称平剧了,也有称国剧的,不过口头上还是叫京剧、京戏的多。剑佩平剧团的台柱是花旦筱毛剑佩,记得还有李荣威、筱毛剑秋、钱美云、曹百岁等,阵容整齐,总体上虽比“西南”、“云南”两家稍逊,但勉强说也算鼎足而三。稍后祥云改为电影院,这一干人马迁驻“春明”,接着名红生刘奎官又来加盟,实力大增,完全可与“西南”、“云南”两家抗衡了。不过对年少的我来说,当时的兴趣全在两位武生,对花旦、红生尚未特别留意。
自从关肃霜、于素秋一来,我的兴趣一下子就转过去了。那是1949年夏秋间,“西南”从汉口请来关肃霜,“云南”从香港请来于素秋。关肃霜是多面手,文武花旦都行,青衣也拿得起,兼擅小生。此前除汉口、长沙外,还跑过上海大码头,初步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一来昆明就推出《大英节烈》、《红娘》和《金山寺》,好像还有比较海派的《新十八扯》和《新盘丝洞》。“西南”在东寺街那边,离我家太远,去的次数不多,起先印象也不很深,当时最深的印象来自于她的巨幅海报。那海报贴在近日楼背面的大墙上。近日楼是昆明的南城门,今已不存(不是东寺街那边新弄的假近日楼),具体位置在近日公园的北侧。关肃霜的“肃霜”两字右边都带鸟字旁,写作“ ”,一般人都认不得,查字典才晓得那是一种水鸟。加上当时还没简化汉字,关字写做“关”,三个字的笔划都多得很,反倒一下子就过目不忘。过几年“ ”的鸟字旁去掉写为“肃霜”,再后“关”简化为“关”,笔划更少,以后就一直写作“关肃霜”。
于素秋比关肃霜来昆稍晚,好像晚不了一两个星期,又都是花旦,所以自然形成唱对台戏的局面,这让昆明戏迷好兴奋。听说抗战中期昆明来过一个“厉家班”,十分轰动。这个厉家班是实力雄厚的国内知名大剧团,成立于南京,拥有文武老生厉慧良、文武花旦厉慧敏等一系列名角大腕,听说他们是兄弟姊妹,更增加了兴奋点。我那时尚幼,虽能恭逢却未能亲睹其盛。不过我设想,厉家班的盛况肯定不及于、关两位花旦的对台戏那么让戏迷兴奋。于素秋也是文武花旦,一来就拿《斩经堂》、《盘丝洞》亮相。据当年的资深戏迷议论,两人各有千秋,比较而言,关的功底更为扎实,唱、做俱佳。于擅做戏,也更海派更摩登;何况于的搭档有名丑梁次珊,名净裘世戎,阵容上更显声色。另一重要原因是于素秋拍过电影,当时“大光明” (今“星火”)同步推出于的片子,在声势上占了上风。印象中梁次珊在性感影星白光主演的《荡妇心》里也演过一个角色,片子在那前后也在昆明上映。这可见于素秋是很会造势的,在市场运作上很有一套。而关肃霜虽能凭自己的实力征服正宗戏迷、票友,在造势上却差了一环,风头上自然就弱了。不过于素秋在昆明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好像是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的头一两天就神秘地回了香港。而关肃霜没走,她后劲大,凭自己的艺术辐射力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声誉日渐飙升,最终在昆明站稳脚跟,并且落地生根,渐渐形成中国京剧的一个流派,从昆明走向了全国。
于素秋、关肃霜的对台戏正唱得热火朝天,老生泰斗马连良应邀从香港来昆明作短期演出。马连良的大名如雷贯耳,其唱片已在云南风行多年,如今能一睹泰斗风采,戏迷、票友兴奋异常,一时间将两位花旦的对台戏都几乎忘了。由于马连良的演出地点是在云南大戏院,让于素秋、裘世戎、梁次珊等组成为马氏配戏的班底顺理成章。于素秋等能有机会与大师同台演出,其兴奋的程度恐怕也不在戏迷、票友之下,所以十分卖力,在《龙凤呈祥》、《四进士》和《法门寺》那些戏里,均有上佳表演。就于素秋来讲,单从与关肃霜唱对台戏的角度看,事实上也沾了马连良很大的光,等于借了马连良的力。关于这一层,戏迷们说起来眉飞色舞,兴味无穷。不过戏迷们也到不是只拿两花旦的对台戏开心,他们对马连良崇拜得五体投地,说马的拿手戏《借东风》如何拿手,举手投足如何如何,津津乐道;讲马氏如何前演鲁肃后饰孔明,头头是道,那个劲头,那个兴奋,是绝不亚于数十年后昆明球迷佩“皇马”侃世界杯的。
在此盛会之前,昆明演京戏的地方虽说有三四处,实际上是以西南大戏院为重镇,而在马连良闪亮登场以后,昆明京戏的重心就很自然地转移到了云南大戏院了。没多久马连良、于素秋先后返回香港,关肃霜移师“云南”升帐,历数十年长盛不衰。
马连良之后一两年吧,另一老生名角唐韵笙率团来昆演出。关于京剧老生,当年有“南麒北马关外唐”之说。麒即麒麟童,也就是周信芳,为南派老生之代表。马连良不用说。唐韵笙雄踞东北,在全国也是叫得响的人物。我弄不明白的是,唐韵笙在昆时间大概也有年把,与实力不俗的刘奎官、筱毛剑佩还合作过不短一段时间,虽说也博得正宗戏迷一片赞誉,但与马连良在昆引起的那种震撼式轰动确实不好比,应该说落差不小。他们开头在云南大戏院演,后来却去正义剧场将就,那地方原本是个舞厅,在长春路往马市口走的拐角处,也就是前几年新建牌坊的东侧。那场子太小,从人行道走过都听得见里面锣鼓响,在那里演实在有些掉价,后来转到“春明”那边与刘奎官他们合作境况才好了一些。我去看过几回,印象较深的是《四郎探母》、《徐策跑城》和《武家坡》。不过那时太过年少,哪晓得人生况味,耳朵听着“一马离了西凉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或杨四郎那几句“我好比”:“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分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听是听着,长辈人说北马如何关外唐又如何,其实能懂得什么。那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觉得武打没意思要看花旦了,听老生嘛还嫩了点。
程砚秋也来过,时间似乎比唐韵笙略早。程砚秋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齐名,世称四大名旦。事过五十多年,我至今不明白自己何以对程砚秋印象不深,也许是自己弄不到票一场也未看过吧。不过程砚秋名气太大,看不上戏也晓得程砚秋来昆明这回事。
那时候我是筱毛剑佩的小戏迷。这有点偶然。筱毛剑佩来昆明要比关肃霜、于素秋早一两年,只是一直不很得势。刚来没多久就碰上个金素秋。金素秋早有名气,1927年就应邀赴日本,在福冈博览会上表演京剧三个多月,成为我国京剧女演员出国演出的第一人。而且金素秋不光能演,还能编能导,人家在“云南”献艺,筱毛剑佩和她那个团就只能呆在“祥云”了。南强街、祥云街那地面早年叫南教场,由兵营演变为市井,三教九流乱糟糟的有些像北京的天桥。后来关肃霜、于素秋来了红红火火地唱起了对台,筱毛剑佩被晾在一边更没戏了。再后“祥云”要改放电影,只好再迁到民生街的“春明”。这边靠近劝业场、武成路也不算冷清,场面档次毕竟又下了一层楼。不过这对我却有利,一是离家最近,二是票价低。
筱毛剑佩唱做俱佳,扮相俊美,虽未大红大紫,却也有自己的一角天地。记得文明街小银柜巷口有家照像馆,临街的橱窗里就摆放着筱毛剑佩的时装玉照,惹得过往行人都少不了要瞟上几眼。迁到民生街“春明”这边后,剑佩平剧团的这位当家花旦,几乎天天都要从我家门前走过,成了福照街一道亮丽风景。隔壁邻舍的街坊和我们家都是不买票的看客。
去“春明”看戏自然是要买票的。与“云南”、“西南”不同,“春明”有楼厅。听说外国剧场包厢特贵,“春明”的楼厅却便宜,去早点买着楼厅第一排,也等于平民价位贵族享受了。
筱毛剑佩的戏路比较对青年观众的胃口。《玉堂春》、《红娘》和《思凡》这些传统戏码自然拿手,演《大劈棺》、《纺棉花》更是她出彩的看家节目。不过筱毛剑佩总是不得意,五十年代初就离开了昆明,但不是去上海、香港那些大码头,而是去的下关,也有人讲是个旧,反正还在云南。以后再无消息。说来也巧,前些年市政协开会认识资深报人陈尚云先生,知陈君也是一位戏迷,得闲就讲起昆明梨园旧事,东说西说扯到筱毛剑佩,陈君居然晓得这位女伶如今在山东济南,说休自然早退了,他前几年去济南旅游时曾去拜访过,筱毛剑佩对数十年前的昆明戏迷居然还记得她,甚感欣慰。连我也觉得欣慰,挺感动的。
这些都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一鳞半爪的。人到一定的年纪难免回眸想往事,旧影浮现了也要沉思一下问个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啊,昆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京戏?其实岂止昆明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讲云南也大体上是这样。前几年我写过一篇东西叫《“昆明像北平”考》,说三十年代及抗战时期不少作家、教授如冰心、老舍、陈寅恪,他们在昆明生活过一段时间,或来讲学、旅游,在他们写的诗、文里,都说昆明像北平(北京)。我就此作了一点小考证,说老舍他们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昆明的建筑和街景,但那只是“硬件”。我补充的是,昆明之所以像北京,与昆明的文化氛围这种“软件”也有相当的关系,具体说就是京戏在昆明的盛行。
京戏在昆明的盛行比前面讲的四十年代末要早。据专家研究,京戏入滇可追溯到1906年,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奇怪的是京戏来了十年就对本乡本土的滇戏呈压倒之势,在昆明稳稳地占了上风,而不仅仅是占一席之地。到了抗战时期,连保山、昭通都出现专演京戏的剧场。此一趋势到解放后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就全省而言,京戏的覆盖面要比滇戏、花灯这两种云南地方戏要小得多,但专业京剧团在全省的分布确实让省外人士感到惊讶。那时昆明除省、市两级各有院、团外,军区还有一个国防京剧团。省会之外,昭通、曲靖、个旧、文山、玉溪、下关,还有东川,都有专业京剧团。到了九十年代当然不能和以前比了(全国皆然),但全省尚有四家专业京剧团。一个远离北京的省份有如此之多的京剧团,实为整个西南、西北所仅见,即使在华东、中南,此种情形恐怕也不会很多。可以这样讲吧,京戏在云南,尤其在昆明的长期盛行,虽说与抗战时期外省人的大量涌入有相当关系,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根据是抗战之前京戏就在昆明盛行,那时候外省人并不多;日本投降后外省人绝大部分都回老家去了,而京戏在昆明的热度不但未降反倒更升。其实云南的汉族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如瑶、苗、壮等族),从根子上讲,都是先先后后从内地或者说从中原(广义的)迁来的移民,都是“外省人”,“中原情结”很强,换个说法就是向心力强。因此,外省人来到昆明不觉得陌生,像老舍、冰心那样见多识广、感觉敏锐的作家还觉得昆明像北京,而所谓“像”绝不仅仅是房子像,牌坊像,街道像。单就抗战时期那个特定时段而言,作为“国剧”的京戏在昆明的盛行,实际上也是昆明人、外省人中华意识和爱国情怀的一个投影。
接着说京戏的票友和戏迷。他们是京戏赖以生存和盛行的土壤。
想当年,昆明京戏的戏迷和票友实在是多。过远的情形就不说了,只讲抗战前后。京戏票友组织习称票房。参加票房的多为军政人士和社会公教人员。当时最有名的票房是公余雅集社,人员以军政上层偏多,他们在“公余”之际也要“雅集”一下。这些“雅集”之士中有好些都是厅长、师长什么的。专家型的票友也有一位,叫陈豫源。陈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大师熊佛西。陈应召回滇任省教育厅艺术专员,与另一位专员王旦东负责筹办艺术师范和金马剧社,艺师成立后任戏剧电影科的班主任。陈豫源学的是话剧,造诣深厚,是云南省第一位科班出身的现代戏剧教育家。同时陈也喜京剧,青衣、小生都拿得起,是一位口碑极佳的票友,他加盟雅集社,贡献良多。
“厅级”票友中缪云台很可注意,这位票友京滇两栖,既喜京剧,更爱滇戏。缪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龙云时期任地矿厅长和富滇新银行行长等要职,见多识广,爱好广泛。这些上层票友经济条件自是优裕,他们不光聚会清唱,还发展到粉墨登场,角色不齐就请专业演员来配戏。他们还派专人赴京、沪购买崭新考究的全部行头和“守旧”(戏曲舞台上用的绣有图案的幕),活动地点在绥靖路东道巷通海会馆的大礼堂,那地方在今天的长春小学对面。另一个可注意的人物是龙绳曾。他是龙云第三子,世称龙三,是相当典型的衙内式花花公子,不务正业,惟热心玩票,自号凌霄馆主,据说他学谭派老生已达相当水准。
抗战后期,西南大戏院请来了色艺双全的花旦金素琴,颇受观众欢迎。有一回云南省新闻记者公会在“西南”举行京剧晚会,西南联大吴宓教授等名流应邀前往观赏。那晚的压轴戏是全本《王宝钏》,由金素琴与唱老生的女票友觉云馆主联袂主演,由此可见金氏在昆明剧坛之地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一时期票友喜与名伶同台献艺的风气。
当时来昆明的外省人相当多,京戏票友里面就有一些是上海或京津那边来的,有些还是名票。如前面提到的觉云馆主,姓杨,来自上海,她唱老生不让伶人,《辕门斩子》中饰杨延辉,得行家首肯。江小鹣也是一位上海名票,早年留法学美术,回国后任上海美专西画教授和教务主任,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先行者之一。江小鹣二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组织沙龙式的天马剧艺会,他是世家子弟不缺钱花,沙龙开支全包了。江氏与诗人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及“第三者”翁瑞午都很熟,在他组织的一次票友演出中,他们四位还演了一出《玉堂春》,陆小曼自然是女主角苏三,翁瑞午饰男主角王金龙,徐志摩演红袍,江小鹣饰蓝袍,结果闹成绯闻,上海小报大炒特炒。抗战初期江小鹣来昆明建了一个铸铜厂(他热心复制古铜器),很投入,还要搞国画展览,不时也参加义演。江氏住在东寺街昆福巷,那是一条小巷,在西南大戏院斜对面。江氏住宅叫平安第,条件不错,艺术、学术界友人常去他家聚会,像是上海沙龙搬来昆明。令人惋惜的是这位艺术家为铸铜厂辛劳过度,1939年在昆明去世,年仅45岁。
风气中也有不好的东西。举个例。龙三与他大哥龙绳武(师长)同时垂涎金素琴,醋海风波发展到两人的侍从间恶语相向,闹得满城风雨。这可苦了夹在中间的金素琴,据说曾打算在教育界找个人嫁了算了,未果,最终还是离开昆明,实质上等于逃离。
但正气还是有的。抗战开始,滇军六十军和五十八军出师抗日,公余雅集社为欢送出征将士接连搞了几次京戏晚会,身为新编十一师师长的鲁道源也参加演出。鲁是滇西昌宁县人,讲武堂毕业,喜京戏,工铜锤花脸,那晚演《霸王别姬》,饰项羽,据说学花脸泰斗金少山颇得韵味二三。鲁师长率部奔赴前线转战湘赣间,战绩颇佳。更难得的是他还将自己的爱好带入军中,组织了一个春秋剧团,下分京剧、话剧两队。为表重视,团长还由他自己兼任。剧团经常在战斗间隙为军民演出,以鼓舞士气民心。
一支滇军部队的“文工团”有话剧队不难理解,话剧擅长宣传众所周知;有京剧队就不容易了,这除了说明这位将军(后升任五十八军副军长、军长)懂得以文艺为武器的宣传之道外,还说明京剧在云南的影响确实是大,它已经传播并渗透到了军队。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
还接着说票房。公余雅集社后来散了,龙三等又出面组织“云社”,活动地点在庆云街庆云剧场,社员基本上还是雅集社那帮老票友,陈豫源和几位上海名票也参加了,阵容坚实,可以演《群英会》、《玉堂春》等大戏,折子戏更不在话下。在上层的影响下,一些机关单位和工厂、学校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票房,如昆明广播电台、云南大学、邮政局、电话局、海口五十三兵工厂等,都各有自己的票房,到抗战胜利前后,又有“华社”崛起,由公教人员和小工商业者组成,社员达八十余人,每周聚会三次,且正式备案。其他票房还有“德社”、“聊社”、“昆社”、“复社”、“杰社”等等,大大小小共有十余个之多。名票萧祝久先生是当年广播电台票房的负责人,同时也参加云社活动。
西南联大是否有比较正式的(有名称的)票房我不清楚,但师生中戏迷和行家可是不少,他们经常聚会清唱,在外文系吴宓教授的昆明日记中不难看到这方面的记录。试举三例。1939年4月某日,云南大学法国教授邵可侣在北门街私宅举行法文谈话会,“会中北大诸男女生唱京戏”。1940年8月某日,又有联大若干师生在南通街(俗称羊市口,连接顺城街与东寺街)某宅楼上聚会唱京戏,操琴的是外文系毕业留校的杨周翰(后来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主编《欧洲文学史》),中央电工器材厂的颉某与著名女票友啸天馆主清唱。1941年7月某日,若干联大师生在北门街张维翰的私宅螺翠山庄举行茶话会。张是大关县人,留日,二十年代任昆明市长,晚年任台湾“监察院”副院长。当时张氏在重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螺翠山庄部分房舍租借他人,西南联大历史系毛 教授(留德)及他们的中德学会都在那里。那天的茶话会上,徐某操琴,某夫人唱《钓金龟》和《武家坡》,李赋宁(清华研究生,后来任北大英语系教授)唱《法场换子》。
联大师生不仅唱京戏,还唱昆曲。昆曲是中国戏曲最古老的声腔之一,源远流长,数百年来对京戏及许多地方戏曲都有深而且广的影响,京戏中的许多传统剧目均来源于昆曲。十多年前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价极高。抗战时期在昆明的不少文人学士喜欢昆曲,十分珍视古代戏曲音乐的这份遗产,不时聚会品味,一唱三叹。其中最让人佩服的是数学系的许宝 教授。许氏系留英博士,中国数理统计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科学家会唱的昆曲竟有三百多出之多。无论许氏住青云街靛花巷,或疏散到北郊龙头村,他周围都有一些昆曲爱好者和研习者,其中包括中文系的罗常培、浦江清两位教授,还有沈从文的小姨妹张充和。据浦江清日记,1943年元旦之夜,昆明广播电台(潘家湾)邀请几位联大师生去演播昆曲,节目有联大同学的《南浦》,张充和的《游园》和吴某的《夜奔》等。浦江清那晚也去了,是“帮腔吹笛”。浦氏在中文系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研究昆曲相当精深,所以对唱曲的要求就比较高。他对那天演唱的评语是“不甚佳”。联大学生中喜欢京戏昆曲的不少,这一点很可留意,反观今日之学生,以唱几句外文歌曲为时尚,老祖宗的东西还有多少存留于他们的“文化记忆”之中?
到了五十年代,票友、票房那一套渐渐不兴了,但群众性的业余京戏活动还在继续。我这个初级戏迷呢1955年也离开昆明去外省就学、工作,一去就是三十多年。虽说人在外省,对昆明京剧界的新闻、旧闻时不时也还留意一下,晓得关肃霜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演出,还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也知道军区的国防京剧团拥有高一帆、刘美娟等一流演员,阵容可观;后来转业地方,不久又与地方上原有的两个京剧团合组为云南省京剧院,下分三个团。再后弄现代戏,京剧院的《黛诺》、《多沙阿波》上北京接连打响,滇派京剧进一步巩固了在全国的地位。作为云南京剧界的首席艺术家,关肃霜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不仅任云南京剧院院长,还做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不过,这些对我不过是信息罢了,我曾经深受薰陶的昆明那段京戏岁月,离我是越来越远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回来后到处转转,瞧瞧那些唱京戏的地方还在不在。在是在的,只是难认了。云南大戏院改名长春剧场,门面小得没个样子渐渐报废,好在演出大厅的遗体还在老地方。西南大戏院后来不唱京戏唱滇戏,连新盖带翻修变成省滇剧院。民生街的“春明”听说早就变了,新门开朝福照街(五一路)那边,变成适应市场的“新潮歌舞厅”;前两年再变,又成了“福照街家常菜”。为省京剧院新建的昆明剧院原本蛮好的,无奈市场不景气,剧院已变成多功能,弄不懂里面在做什么。
1992年关肃霜逝世。昆明京戏的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
我继续寻找过去岁月留下的遗痕。在一些戏迷同学的身上,我找到了。这与昆一中的传统有些关系。
昆一中创建于1905年,今年适逢百年大庆,是昆明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昆一中的体育运动是有传统的。早在1948年,昆华中学(昆一中前身)足球队就与球王李惠堂的球队比赛过,虽败犹荣。五十年代前期,昆一中又出了杨伯镛(中国男篮主力,中国女篮主教练)、马克坚(中国足球队守门员,中国足协秘书长)等一系列球星,广为人知。昆一中学生喜欢体育,并且形成传统,可能与学校历来不兴招女生有些关系,没有女生分散男生的注意,下了课都去打球。五十年代末一开禁,招了女生,体育传统不彰,是否可作反证?这是戏说校史,不必较真。其实昆一中的学生也不是只会打球,许多学生还喜欢京戏,会拉会唱的很不少,形成一个戏迷群。这与名票萧祝久先生有相当关系。
萧祝久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名票,他后来离开电台来昆华中学任教。我有幸进入这所中学读书,萧老师教过我们班的生物课。学校每逢开晚会萧老师都要露一手,印象最深的是《打渔杀家》,萧老师唱萧恩,我的同学马登融君唱桂英。昆一中找女角比较困难,马登融爱唱京戏,擅演花旦,宝贝得很,后来他与萧老师还去胜利堂演过。
萧老师是昆明人,生于1912年,抗战前就读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听说萧老师在济南时常与当地名票交往,这段经历想必与他日后的票友生涯有极大的关系。萧老师唱小生享誉昆明票界乃至梨园,他的《贩马记》听过的人无不叫绝。其实萧老师早先学的是青衣,宗程派,后来才唱小生,之后再改攻老生,唱什么是什么,在昆明票界无人能及。萧老师还擅昆曲,听说常有行家登门求教。不独此也,萧老师绝对是多面手,样样来得,文场(戏曲乐队的管弦乐)武场(打击乐)都拿得起,此所谓“六场通透”。我对这些其实外行得很,都是从深谙此道的老同学白如锡君那里听来的。
昆一中的票友不止萧老师一位。听另一位老同学朱瑞麟君讲,当年(五十年前)昆一中有“一中五名票,二杨邓顾萧”之说。除萧外,顾指教数学的顾传澍老师,邓指教导处的邓公略老师;二杨中的一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另一位是教俄语的杨可大老师。听说这位杨老师抗战前就去过苏联,与党史上很有名的那二十几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些关系呢。不过我与这些票友老师无近距离接触,具体印象已很模糊,倒是教历史的胡肃秋、黄清两位老师我还记得他们喜欢京戏,时不时来段清唱,票友好像还算不上,但在晚会上也露过脸,胡老师唱青衣,黄老师唱老生。胡、黄两位老师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同班同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毕业的金录萱老师会打小锣,场面上也是少不了的。
我的同学里爱看京戏也会哼几句过把瘾的很多,这只算戏迷。能做票友登台的却不多,以前只晓得马登融,这些年才知道还有好几位。一位是马国良君,他是盘龙业余京剧社的票友,工老生,拿手的是《洪羊洞》、《搜孤救孤》和《捉放曹》里的唱段。大凡同学聚会,马君差不多都要来上两段的,听得众人喜洋洋地拍巴掌。
我想了解一下现今的票房怎么活动,去盘龙票社旁听过几次。一看真开了眼,票房火着呢。现在不叫票房叫业余京剧社,简称票友社或票社。一问,昆明的票社多达二三十家,票友上千。大些的像盘龙票社、五华票社,下面还分成几个团。马国良君所在的盘龙票社原以文明街的盘龙区文化馆为活动据点,前不久迁到星火剧院,更上了两层楼。这家票社颇具实力,著名老作家苏策先生的夫人刘竹娟女士是省社科院地方志编委会处级调研员,酷爱京戏,工青衣、花旦,去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戏迷俱乐部大赛,彩唱《武家坡》,荣获二等奖,十分了得。
除五华、盘龙两家票社外,其他还有艺术家同盟艺术团、春城文艺之家、益友票社、金马剧社、昆钢京刷团、市老干部京剧团和大专院校京剧团,等等。票社一般每周活动一次,各有各的据点,反正不外乎文化馆、文化宫、俱乐部、单位舞厅小礼堂以及街道办事处的文化活动室之类场所,像萧老师他们就常去五华医院背后染布巷那里去玩。去露天公园的也很不少,尤其是翠湖。票社间也交流比赛,互赠锦旗,旗上写着“弘扬国粹 振兴京剧”、“老有所乐 弘扬国粹”、“振兴京剧作贡献 自娱自乐夕阳红”等;单联独句的也有,如“戏迷之家”、“国粹沟通票友情”之类。从这些文辞可看出现今的票友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视京剧为国粹,要出一把力振兴它。“兴”就不消“振”了,不“兴”才要去“振”。毕竟风光不再,很无奈的。
不知什么原因,同学中真正能唱的不是很多,能操京胡的可是不少。魏天祥君能拉会唱是个全才,但后来向操琴倾斜,在戏迷同学中影响日增,只是轻易不愿展示。魏君家住文林街师大附中宿舍,分了面积更大的住房也不想搬走,说住在文林街好,离翠湖才几步路,“翠湖等于是我的”。后来我才晓得,这位老同学几乎天天都要去翠湖玩,在观鱼亭附近自拉自唱怡然自得。翠湖唱京戏的戏迷、票友不少,已形成相对固定的“部落”,一圈一圈的。据闻魏君不想加盟,大约是嫌不自由吧。我听九龙池那边两位五华女票友说,她们几次去观鱼亭那边转悠,想找机会唱两段请魏君操琴,可魏君仍只顾自拉自唱,陶醉得很,不知旁边有人。互动终于未能发生。
白如锡同学操琴名声更大,别说在翠湖的京戏圈内外一说白老师无人不知,在昆明票界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一些戏迷、票友对他的琴艺佩服得很。前些年没退休还上课,一到周六周日,戏友们一早就登门来请:“走,白老师,中午饭给家首说一声就不消管啦,走!”
杨其同学是云南体坛名宿,五十年代省排球队主攻手。文武全才,也善操琴,成名比白如锡要早,如今是盘龙业余京剧社的琴票,同学聚会时与马国良一拉一唱,珠联璧合。他还是“盘龙”的两位副社长之一(另一位是刘竹娟女士),分管文武场,热心热肠,乐此不疲夕阳红。
朱瑞麟同学更是了得,读昆一中时即已成名,上清华的时候还参加了学校文工团京剧队,读书玩票两不误。朱君长期在外工作,这几年嫌杭州太热在昆明买了房子夏天与夫人来避暑,并与昆明票友及同学相聚。我问老同学还玩票吗?说不玩了,如今自己动手做京胡。问其故,说女儿在北京,有次陪他逛琉璃厂,女儿说爸爸要琴我给你买一把。做父亲的很感动,说小时候爸爸给你买玩具,现在轮到你给爸爸买“玩具”了。
我听了也很感动。人老了,也该玩自己想玩的“玩具”了。老同学告诉我,琴还拉,但做琴成了他的新爱。女儿花一千多元买的琴自然不错,何况还是他亲自挑的。回家摩挲把玩,觉得这样的琴自己也可以做出来。还真做出来了,有的还送给琴友,甚得赞誉。几年前朱瑞麟选上好的香妃竹特意做了一把送给萧祝久老师。老师拉了拉,很喜欢。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2003年,高寿九十有二的萧老师在云大医院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段岁月。据同室病友讲,萧老师在病房中仍不忘西皮、二黄,不时浅唱低吟,回味人生。但毕竟人生苦短,萧老师终于驾鹤西归,带着他的票友岁月,带着他的京戏梦幻。
我有幸在昆华中学/昆明一中读书六年(1949—1955),恩泽深受,终生不忘。欣逢母校百年大庆,特作此文呈诸师友哂正,并表纪念之情。
作者:余斌 本文发表于《滇池》2006年第1期
余斌, 人文学者、云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1949年进入昆华中学(今昆一中),1955年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兰州从事文艺、教育工作30年;上世纪80年代末回滇任教;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和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论文《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1984年获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等论著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教师三等奖,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